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:从“爵—食体制”到“爵—秩体制”(第15/25页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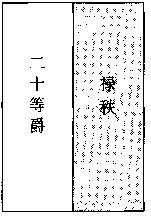
秦汉爵—秩体制
魏晋以下出现了九品官品。“官品体制”的性质,我们认为是“官本位”的,详见本书上编第六章。“官品体制”也是“一元性”的,因为其他各种位阶序列,都被纳入了官品架构之中,或通过与官品挂钩而获得了关联性和可比性。与“官品体制”不同,秦汉“爵—秩体制”下,二十等爵与禄秩呈疏离之势;无论从序列间的链接、搭配看,还是从品秩要素的配置看,都没形成严密的一元化整合。“爵—秩体制”由此显示了某种“二元性”。下面,就对这一点进行讨论。
上节论及:在“赐满”制度下,二十等爵并不跟所有秩级一一挂钩,而是只跟秩级的几大层次挂钩;挂钩的中介是公、卿、大夫、士概念——爵有公、卿、大夫、士几大段落,秩级也有公、卿、大夫、士几大层次。“赐满”以“层次”为单位而沟通爵、秩,意味着它主要用于处理官僚身份,官僚身份分为几大层次,礼制待遇和法律特权依此层次而定。如福井重雅所论:“汉代上级官吏所被给予的礼制上的荣誉和刑法上的特典,必须作如下的理解:他们也许并不来自于六百石的官秩,而是实际上根本存在于五大夫的爵位。”(74)
若换个角度看爵、秩关系,不以“层次”为单位,而是以“级别”为单位,即从爵级和秩级是否“级级对应”来观察问题,在二者间又能看到什么呢?
首先讨论“爵、秩相比”现象。在确定薪俸、特权、待遇、资格等“品秩构成要素”时,当局面对着爵、秩两个序列,往往有必要以这个“比”那个,从而把二者联系起来。通过那些爵、秩相“比”的“点”,就可以看清两个序列是如何链接起来的。可供分析的有四种“比”法:第一是《二年律令》传食规定中的爵、秩相比,第二是《二年律令》赏赐规定中的爵、秩相比(75),第三是汉元帝时十四等嫔妃的视若干石、比某某爵的规定(76),第四是汉成帝对出资者赐爵补吏的规定。下将四者一并列表,并列入“赐满”制度以便比较:

续表

第1种传食和第2种赏赐,都是先就“秩”做出规定,然后用“爵”去“比”的。观其“比”法,明显与“赐满”制度不符。按照“赐满”制度,“卿爵”是中二千石之爵,五大夫是六百石以上官之爵;而《二年律令》的传食待遇却是“卿以上比千石”,“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”。赏赐时的以爵比秩,比传食的“比”法更细密,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,卿比千石,五大夫比八百石,公乘比六百石,公大夫、官大夫比五百石,大夫比三百石,不更比有秩,簪褭比斗食,上造、公士比佐史。李均明先生说:“二十等爵中,‘五大夫’属划等中的临界性爵级,涉及具体权益时,大多属下,……有时亦上挂。”(77)“临界”时的忽上忽下主要在以爵比秩时发生,爵级本身并没有忽上忽下。以爵比秩时的忽上忽下,表明爵、秩之间本无定“比”。
汉元帝为嫔妃确定了十四个等级,形成了第3种“比”法:昭仪位视丞相,爵比诸侯王;婕妤视上卿,比列侯……直到少使视四百石,比公乘;更低的五官以下的段落,就不比爵了,只“视若干石”而已。那么在“卿爵”即左庶长至关内侯的段落,最低的是“良人视八百石,比左庶长”。中二千石列卿赐爵左庶长,良人视八百石,却也“比左庶长”。那么左庶长是对应中二千石,还是对应八百石呢?显然没有固定的对应,而是依场合做个案处理的。
最后第4种也许不算是“比”,但可以反映在“官资”要素的配置一点上爵与秩是什么关系。对向朝廷入谷者,汉成帝加以褒奖,其办法是赐爵和补吏,赐爵右更的只补三百石吏;赐爵五大夫的补郎。那么我们来看,郎官的自身秩级是比三百石。右更与五大夫差5级,而且一属卿爵、一属大夫爵,而三百石与比三百石却只差一秩。
在以上四个爵、秩相比的例子中,我们看到的爵、秩关系是错综不一的,这表明爵、秩间并不存在级级对应的关系,而是因时因事而变的。“爵”与“秩”之间的错综不一的状态,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?有。它既不同于周朝品位秩序,又不同于魏晋以下的“官本位”秩序。魏晋的爵级已被列于官品里面了,爵、品间存在着明确清晰的对应关系。据《魏官品》,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在第一品,县侯在第三品,乡侯在第四品,亭侯在第五品,诸关内侯、名号侯在第六品(78)。李唐封爵之制,王正一品,嗣王、郡王、国公从一品,郡公正二品,县公从二品,侯从三品,伯正四品上,子正五品上,男从五品上(79)。这时各种礼遇都可以根据官品推算,即便对爵级的相关待遇有特殊规定,在级差上也有比例可循。